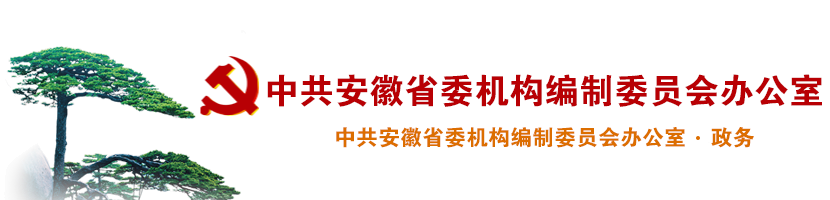“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現的貧困,包括消除極端貧困,是全球最大的挑戰,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必不可少的要求。”2015年,這句話莊嚴寫入聯合國《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》。僅僅五年后,中國便以一份舉世矚目的成績單,提前十年兌現了這份承諾: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,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,12.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。這份“高分”答卷,不僅標志著中華民族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大步,更以其空前的規模與速度,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。
這一奇跡的誕生并非偶然。我們立足我國國情,把握減貧規律,出臺一系列超常規政策舉措,構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體系、工作體系、制度體系,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,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。這條道路突破了西方減貧模式的路徑依賴與思維定式,用中國實踐,為全球貧困治理貢獻了智慧和方案。
中國特色減貧道路何以能走通?其根基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。具體而言,它體現在強大的資源動員與組織執行力上。錢往哪里投?戰略重點清晰明確。近1.6萬億元的財政資金精準滴灌,瞄準脫貧靶心,確保藍圖繪到底,不走樣、不變形。人往哪里派?黨員干部沖鋒在前。25.5萬個駐村工作隊、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,毅然奔赴最偏遠的山村,堅守在脫貧攻堅的第一線。“全國一盤棋、全民一條心”的動員力,破解了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“政策懸浮”困境,為大規模、區域性整體性脫貧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堅持精準扶貧、精準脫貧,是中國反貧困的成功經驗。它摒棄了“大水漫灌”和簡單套用外來教條的做法,將目光聚焦于貧困老鄉的灶臺炕頭、田間地頭,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務實作風。這一方略貫穿于脫貧全過程:在識別環節,我國創造了“建檔立卡”這一精細化管理工具,通過“一進二看三算四比五議六定”的精準識別法,建立起覆蓋全國的信息系統,確保了扶貧資源真正流向最需要的群體。在幫扶環節,量身定制“五個一批”組合拳。無論是四川涼山“懸崖村”村民告別藤梯、搬進縣城電梯房的易地搬遷,還是甘肅隴南的年輕人通過直播帶貨將土特產賣出深山,都是因地制宜、因戶施策的生動寫照,成功將外部的“輸血”轉化為內生的“造血”功能。在退出機制上,更是用“鐵尺子”量出真脫貧。建立了嚴格的收入標準和“兩不愁三保障”多維指標,并引入第三方評估嚴格考核,堅決杜絕數字脫貧和虛假脫貧,確保脫貧成果經得起歷史和人民的檢驗。
精準扶貧方略落地生根,離不開政府、市場、社會協同發力的大扶貧格局。它突破了單一依靠政府或市場的傳統模式,形成了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減貧合力。一是“扶貧先扶志,扶貧必扶智”,著力激發內生動力。中國的減貧實踐深刻表明,不僅要解決“口袋窮”,更要根治“腦袋窮”和“能力窮”。一人就業、全家脫貧,增加就業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增收方式。以“雨露計劃”為例,通過對貧困家庭的新生勞動力進行職業技能培訓,使他們成為脫貧致富的“先鋒隊”,有效阻斷了貧困的代際傳遞。這一幫扶計劃,在脫貧攻堅期間,累計惠及800多萬貧困家庭新成長勞動力,帶動1500多萬貧困人口脫貧。二是依托東西部扶貧協作與對口支援機制,實現先富幫后富。這一機制跨越了地理與行政界限,將共同富裕的愿景轉化為扎實行動。“閩寧模式”便是典范,福建帶著資金、人才與技術,在寧夏的戈壁灘上建起現代化產業園,真正讓“干沙灘”變成了“金沙灘”,為破解區域發展不平衡難題貢獻了中國智慧。三是廣泛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參與。在政府引導下,從“萬企幫萬村”的產業聯動到深入社區的消費扶貧專柜,從公益人士的直播帶貨,到奔赴鄉村的志愿支教,扶貧工作從一項國家責任升華為全民參與的共同使命,生動詮釋了“人人皆愿為、人人皆可為、人人皆能為”的社會幫扶理念。
中國實踐讓世界看到:貧困不是宿命,只要方向對、方法對、意志堅定,弱鳥完全可以先飛、高飛。中國實踐提供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、行之有效的路徑選擇。不僅如此,中國正以高度的責任感,將自身的減貧經驗轉化為惠及世界的公共產品。中國已為全球180多個國家和組織開展約1.5萬個援外人力資源開發合作項目,累計培養各類人才50多萬名,有效提升了各國相關領域發展能力;通過實施零關稅待遇,中國為最不發達國家、特別是非洲國家打開了廣闊市場;截至目前,中國已向160多個國家提供發展援助,同150多個國家攜手共建“一帶一路”;全球發展倡議提出4年來,已動員230多億美元資金支持全球南方發展振興,開展1800多個合作項目,為破解發展赤字提供有效助力。
脫貧摘帽不是終點,更是新生活、新奮斗的起點。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進程中,中國減貧實踐正從消除絕對貧困向緩解相對貧困、促進全面發展邁進,持續積累新的治理經驗。未來,中國將繼續通過“一帶一路”等合作平臺,與世界各國攜手,為建設一個沒有貧困、共同繁榮的人類社會貢獻智慧與力量。(作者:張春敏、吳歡,分別系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院長、教授,中央民族干部學院助理研究員)(光明日報)
信息來源:人民網